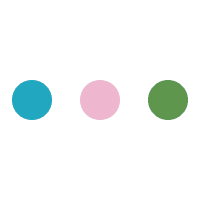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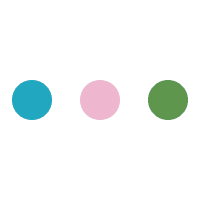
But my pride was soon humbled, and a Sober melancholy was spread over my mind By the idea that…whatsoever might be the Future fate of my history, the life of the historian must be short and precarious
——Edward Gibbon
山勢犀利覆額,陡峭的
少年氣象不曾迷失過,縱使
貫穿的風雨,我在與不在的時候
證實是去而復來,戰爭
登陸和反登陸演習的硝煙
有時湧到眉目前,同樣的
兩個鬢角齊線自重疊的林表
頡頏垂下,蔥蘢,茂盛
而縱使我們的地殼於深邃的點線
曾經輪番崩潰,以某種效應
震撼久違的心——
髮彼兩髦
實維我特。我正面對著超越的
寧靜,在這裏窗下深坐
看大寂之青靄晨光中消遙
閒步;
北逾奇萊
南止於能高山之東
衣領挑達飄揚
然則高處或許是多風,多情況的
縱使我猶豫畏懼,不能前往
想像露水凝聚如熄滅的燈籠
鳥喙,熊爪,山豬獠牙,雷霆
和閃電以虛以實的聲色,曾經
在我異域的睡夢中適時切入——
多情的魘——將我驚醒,聽
細雪落上枯葉,臺階,池塘
我以為那是恐怖與溫柔
懸空照面,輕撫我一樣的
犀利,一樣陡峭,光潔的額
少年氣象堅持廣大
比類,肖似。然後兩眼闔上……
縱使我躊躇不能前往
你何嘗,寧不肯來,準確的心跳
脈搏?
此刻我侷促於時間循環
今昔相對終於複沓的一點
山勢縱橫不曾稍改,復以
偉大的靜止撩撥我悠悠
動盪的心,我聽到波浪一樣的
回聲,當我這樣靠著記憶深坐
無限安詳和等量的懊悔,仰首
看永恆,大寂之輕靄次第漫衍
密密充塞於我們天與地之間——
我長年模仿的氣象不曾
稍改,正將美目清揚回望我
如何肅然起立,無言,獨自
以倏忽蒲柳之姿
那時候的花蓮,昔日的小城,有若干清潔的河水平行切過,快速切過。我知道所有河水都源自西邊的高山某處,起先或許只是深邃的懸瀑吧,彙集便匆匆趕來,隨地勢蜿蜒再三,乃尋到它必然的方向,朝東急流,穿過人們聚居的小城,于是入海。河水在進入街衢市區以前,自然是清澈光潔的,灌溉了一些阡陌農田,田裏水滿,映見高山巍然在遠處俯視。然而即使在它穿過市區,並且已經接近它全程最後那一段的時候,在昔日那時候,也一定還是清潔的,就那樣保持著它深山谷壑的本來面貌,快樂地注入大海。
我們右邊那排扶桑下只有一條小溪,還不能算是河。小溪流了短短一段路,很快就被農戶築堰改道,引向一水田地帶,竟不知所終——我只記得那裏直塹回塘無數,淺淺的水池與平靜的深潭,春天來的時候到處是蝌蚪。那些蝌蚪起先只搖著尾巴在水裏泅游,過不了幾天小脚生出來了,可是因爲尾巴還在,動起來很尷尬很不方便,鴨子趕來爭食。有一天蝌蚪的尾巴不見了,四隻脚茁壯成長,果然變青蛙了,跳起來比鴨頭還高。那時秧苗已經插好了,遠遠看去一片新綠,甚至還帶著另外一種無法形容好聞的氣味,來自清水和泥土,來自迸生的嫩葉。左側又一排扶桑,過去是鄰居的菜園,緊靠著他們日式房子改裝的大瓦厝。這鄰居姓黃,客家人。他們將瓦厝前進一長條辟爲雜貨店,廊下挂著烟牌,酒牌和鹽牌,主人日夜不停在店裏工作,搬過來搬過去,不苟言笑。他太太偶爾在店裏出現,但平常不是在後進屋裏,就是在菜園澆水灌溉,很有耐心地照顧著那許多種類不同的青菜和瓜豆。我從扶桑枝葉間望去,她沉默篤定周旋于一畦一畦肥腴美麗的綠葉黃花當中,那種安詳勤奮的表情,好像是與生俱來的。黃家瓦厝另外一邊加蓋了一長條鐵皮屋子,沿墻又種了七裏香,開白色小花。再過去才是一條河,一條遙遠自高山來奔向大海的河。
我順著河水向東慢騎著脚踏車。下麵那一帶街道漸行漸寬,屋舍越稀,而海水就在眼前。我左轉進入一條巷子向北,不久就到城隍廟口,然後穿過廣場繼續前行,遇見一條開闊的橫街,街邊是河,過了河那邊岸上又是一條街。這河比其他都大一點,而且河床深陷,兩岸街上沿循都種了垂柳,住宅透過雙重的柳條隔水相望。長巷盡頭地勢升高,有木橋跨過河面,將兩條平行的街道連結起來,欄杆疏落。我轉到對岸一棵垂柳下將車停好,看水。那時四處幽靜聽不見任何喧嘩,太陽正緩緩轉過酒廠的大烟囪,作勢要隱藏到高山之背。是的,靜寂的午後,我只感覺到河水奔走潺潺的力量,好像在回應著某種召喚。河裏有拉長的水草,在陽光下扭動,做出無數不同的姿態,每一秒鐘都在變化。河床上布滿石礫,磊落渾圓,好像在水裏不斷滾動,但那只是我的錯覺。午後的太陽照在水面,粼粼閃光,蜻蜓從這岸飛越强烈的日頭,幾點黑影這樣飄過,眩目,震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