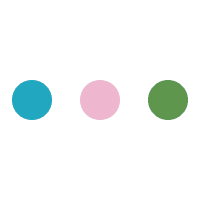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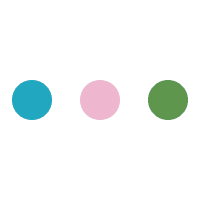
高二那年擔任校刊主編,依例在編輯完成並經指導老師審批核可後,連同封面設計,由我親自交付校方指定的「東益」印刷廠付印。
印刷廠座落花蓮市節約街上,剛好在舊鐵道下方涵洞口附近,騎自行車從博愛街一路到底,常會看見上方台鐵金黃色的柴油列車呼嘯而過,緊鄰的耳鼻喉科醫院樓上則不時傳來生澀的鋼琴聲,形成強烈對比,只是從未有人在意。
當時平版印刷尚未普及,號稱台灣「後山」的東台灣花蓮,印刷廠大多還使用傳統的手工鉛字排版,加上投稿同學不甚工整的筆跡,錯字自是難免,因此校方通常會安排一或兩日公假,讓我跟幾位編輯同學在打樣後,前往印刷廠逐一校對。
如同早期台灣大多數的小型工商業,東益當時也係住商混和型態,即臨路店面作為廠房及辦公區,後方則為住家。主人楊老闆非常親切,不僅提供外賣的小籠包跟水餃作為午餐,看到校刊上我寫的幾首現代詩,他居然興致勃勃,甚至頗為得意地用閩南語告訴我「我兒子也是寫詩的」,隨即帶我到廠後的住家客廳,這下非同小可:櫥窗內赫然有座沈甸甸的「優秀青年詩人獎」,再看得獎人「葉珊」更不得了。
可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原來我才開始寫詩,心儀的幾位前輩之一葉珊居然是楊家公子,詩人的爸爸當非等閒之輩了,頓時對楊老闆的崇敬又多了幾分。由於有這份「機緣」,愛屋及烏的楊老闆特別從書櫃取了幾本葉珊的詩集,都是自家印的,包括《花季》以及他與花蓮在地詩人陳錦標等創辦的《海鷗詩頁》十數份,代表詩人送給我。儘管來不及請遠在美國的作者親自簽名,已讓我欣喜若狂,差點忘了其他兩位編輯同學的存在。
滄海桑田,據說舊鐵道隨著1982年花東新線開通後消失,節約街與博愛街交口的涵洞早已填平作為徒步區,印刷廠也被某標榜懷舊文青風的咖啡鋪子所取代,而後來筆名改為「楊牧」的大詩人葉珊也在去年仙逝:
當晚霞滿天
你駐足,塔影自裙前撤去
山路一片紅暈
你走過的小路,是一條
微醉的斑紋蛇
每次返回花蓮,看到晚霞滿天,我總會想起《花季》書中的這一首詩,那是大詩人年少的創作,也是我第一本擁有的詩集了。不過卻無意再前往節約街一探究竟,怕勾起些許惆悵與感傷。
妻發病以後,除了依照醫生的指示按時至醫院接受化學治療外,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花蓮的老家休養。老家雖然座落市區中山路,花蓮高商對面透天的樓仔厝與鄰近的大樓公寓之間仍留有一方小小菜園,零零落落地種了些小白菜什麼的,地面上則搭了簡陋的竹棚,僅有的一枚幼嫩絲瓜就在那兒孤伶伶的晃呀盪的。
冬天的花蓮海風甚大,每當鐵門咻咻作響,而緊閉的窗戶仍抵不住強烈滲入的風聲淒厲嘶喊時,我總會為那枚絲瓜的命運而捏了把冷汗。
絲瓜倒是一直十分堅強的垂掛著,妻的病情經過兩次化療以後似乎也有了明顯起色,令我頗感欣慰。而且不知道從那一天開始,棚架上出現了一隻伯勞鳥,淺棕色的覆羽,白色的頭部有著清晰細長的黑眼圈,暗紅的長尾隨著啾啾啁啁的悅耳叫聲而幽雅擺動,令人一眼就可以認出,那是一隻紅尾伯勞。
最早與伯勞結緣,約莫在十三年前的初春,那時與新婚的妻共赴墾丁渡蜜月,陽光燦麗的國家公園固然令人心曠神怡,大門外不遠處的景象卻教人不忍卒睹:街道兩旁擠滿了烤小鳥的攤販,一隻隻焦紅的赤裸鳥屍成排地吊掛著,小販且不時拉大嗓門向過往的車輛遊人曖昧的兜售。
其中一位滿口檳榔汁的彪形大漢指著一旁生銹的鐵籠,裡面尚留有幾隻奄奄一息的鳥兒,得意地告知遊客那些都是遠來過冬的伯勞候鳥,他裝模作樣的半掩著嘴放低音調說:「噯呷得卡緊,過了春天就瞴啦,警察最近也抓得緊哩!」
令一旁心疼小動物的妻氣得直發抖,從此對遠來過冬的候鳥總多了一份疼惜之心。
事隔多年,在不算太安靜的市區一隅,看到悠閒自得的伯勞令人興奮:渾圓飽滿的小小身軀在棚架跳上跳下靈活的躍動,濕冷的空氣中彷彿多了透明清亮的小風鈴,為原本單調乏味的菜園帶來無限生機與陶然。儘管我一直無法推斷牠究竟係來自中國大陸北方的候鳥、抑或已在地生根的留鳥,或者是不小心與同伴走失的迷鳥:甚至也不太能確定分辨雌雄。
妻開始能下床走動,只要天氣不太壞,我總會陪她走出屋外散步。紅尾伯勞則固定在每天中午及傍晚準時向絲瓜棚報到,每當清脆的唧啾聲隔著薄薄的紗門傳入,在客廳半臥的妻蒼白的臉上立即顯得精神一振,提醒我攙扶她出去看看,感受那一份恬淡與收斂。
對於早先屏東鄉間濫捕伯勞燒烤出售的情景仍記憶猶新的妻,直覺的認定牠就是逃過大劫的候鳥,而自己也正面臨生命中無可避免的劫數,因此頗有惺惺相惜之心。有次菜園聞風而至了幾隻大肥貓,紅尾伯勞嚇得一連好些天沒來,我們竟也彷彿鄰家走失了心愛的小狗一般,感到無以名狀的失落。
連續假期過後,小小菜園開始有了些春意,不過絲瓜似乎並沒有長大多少,也一直未曾見到菜園的主人,唯一令人窩心的是紅尾伯勞依然每天到訪,無論是否覓食或僅單純做短暫逗留。農曆春節從台北回家時我特別帶了六百釐米的長距鏡頭,嘗試為牠拍攝各種姿態,已經與我建立了小小友誼的伯勞不再怕生,不過卻始終保持固定的安全距離,顯然深知人類的不可信賴吧。
病情看似已經大為好轉的妻,突然在某日起床後因急喘不已而又住進了醫院,神色凝重的醫生告知癌細胞已轉而侵襲擴散至整個肺部,必須仰賴氧氣面罩始能呼吸,並表示情況已不甚樂觀。
彷彿自曙光中突然陷入絕望的深淵,竟日守候在醫院的我依然談笑風生,深怕妻察覺判決的真相,只能在步出病房後悄悄拭淚。偶有返家取物,居然多能在小小菜園與紅尾伯勞不期而遇,無論是否牠已往固定來訪的時段。平日熟悉的百囀千啾,在低落的情緒裡顯得格外悲悽,似乎也深知我無助的愁苦吧?
妻的病情持續急遽惡化,住院後約莫一星期就去世了。無法接受突如其來的殘酷打擊,且過於哀傷的我忙著料理喪事,對於屋旁的菜園視而不見,自然也無心理會伯勞鳥的去向。
及至一切塵埃落定,想起妻一直關切的伯勞,幾度衝出門外苦候搜尋,在牠固定造訪的時段竟然接連好幾天都不見蹤影,棚架上只留下小小絲瓜,竟也已經泛黃枯萎,無助地在微微雨中愈發飄零著孤獨的位置。
所有的巧合同時發生,令人深感世事之無常,忍不住陣陣酸楚相互牽扯,一時都湧上心頭。
已經個把多月了,伯勞鳥從此真的就再沒有出現菜園,是因為春天的來臨而返回北方了嗎?或者移棲至他處覓食,或者已尋得伴侶比翼雙飛遠走他鄉了呢?答案自然是無解的。
直至有天,尚就讀國小的兒子問到「勞燕分飛」的解釋時,我才猛然想起,「勞」指的不就是伯勞鳥嗎?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是否早已提醒我,該是離別的時候了呢?一向善良的妻是否早知自己的病不能治癒,才特別透過小小伯勞來暗示始終抱持樂觀的我,要我及早做好心理準備呢?甚或伯勞根本就是妻的化身,在她病重無法清楚言語時,藉悅耳清脆的鳥語來安慰愁苦不堪的我呢?
儘管今年春天已近尾聲,大部份的候鳥都已整裝北返,我總還是儘可能在都市的每一方空間,找尋紅尾伯勞的蹤跡,希望能再找到一些暗示,也許妻還有別的留言吧?這次,我不應再遺漏些什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