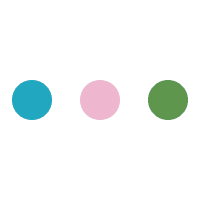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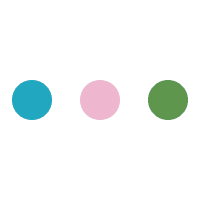
那時正值三十歲,文學為我注滿了樂觀的活力,就像是太平洋上的那輪明月般光輝,我相信未來還有無限的可能,就像是花蓮綠意盎然的大地,七星潭波濤洶湧的浪花,以及鵝卵石生生不息的歌唱,這是一座沒有冬天的國度,所以就連黑夜也是無比的光明燦爛……
花蓮在我童年時的唯一印象就是山高水遠,容易暈車的我,對於北宜和蘇花公路向來充滿了畏懼,九彎十八拐在七○年代盛行的恐怖片渲染之下,更是顯得鬼影幢幢,所以花蓮在我的心中始終是一塊神祕之地,彷彿是位在台灣之外的另外一個陌生國度,從來沒有想過自己這輩子竟會與它結緣。
但命運總是把我們帶到一條不可思議的道路上去,一九九八年我拿到博士學位,畢業後的第一站居然就是花蓮的東華大學,而且在這狹長的島嶼邊緣一待就是十二年,從我二十八歲到四十歲,可以說是人生中最充滿活力的一段黃金歲月。曾經有位篤信伊斯蘭教的好友告訴我,她旅行的方式就是走到公車站,看有哪一班公車來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跳上去再說。我很驚訝她怎麼那麼勇敢?難道不會為未來擔心?她微笑地回答說:「擔心是沒有用的,因為這一切都是真主的安排,該發生的,就是會發生,事前計畫也是多餘。」我非常羨慕她的眼神既清澈又堅定,對於人生的下一秒沒有任何的懷疑,然而回想自己一路走來,不也多是如此?當年毅然決然離開台北,來到人生地不熟的花蓮,不也是抱著一股「看有哪一班公車來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跳上去再說」的傻勁?
但移居花蓮,其實也並非全是偶然,反倒是許多因緣巧妙地聚合而成,讓我不得不真的感激起上帝的苦心安排。那時東華大學才剛成立不到三年,負責創立人文社會科學院的是楊牧老師,他特地從美國返回故鄉,滿懷理想要在這兒打造一座人文藝術的烏托邦,也因此吸引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如中文系的鄭清茂老師、顏崑陽老師、王文進老師,英美系的吳潛誠老師、李永平老師、曾珍珍老師等前來。他們都是學問淵博又熱愛文學創作的師長,共同將這一座位在花東縱谷小而美的校園,打造成一座彷彿與世隔絕的詩人桃花源,讓我不禁深深地為之嚮往。所以也果真是神的安排,東華大學中文系才新成立,亟需要新的教師加入,而我又正好拿到博士學位,天時、地利再加上人和,便開啟了我的花蓮生涯。
那時正是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網路剛剛興起,各種關於未來的預言紛紛出籠,有期待也有恐懼,惶惶不安中卻摻雜了更多的興奮和刺激,周圍和我同輩的人大多來到而立之年,正是蓄勢待發,無一不摩拳擦掌,準備在新的世紀中大顯一番身手。然而二十年過去了,我們也都一起又堂堂邁入知天命的年紀了,才恍然大悟當年的天真和愚騃,我們實在是太過小看了這個世界,所以也都各自吃了些苦頭,多曾被大浪打到谷底過,又掙扎著想要重新冒出頭,但一次卻比起一次來得更加認命、安分,也才體會到了自己年輕時極為喜愛,但如今才真正懂得意義的陶淵明〈自祭文〉四個字:「人生實難」。
但或許該慶幸的是,那時正當壯年的我,躲入花蓮的文學桃花源中,竟彷彿秦人避難似的,悠悠過了好幾年不食人間煙火的清靜歲月,也讓我免於過早的衰敗。我深深記得當時楊牧老師的再三告誡,不管二十一世紀變得如何,我們就是要「唱高調」,不隨波逐流、與世浮沉。「唱高調」這三字對現在的年輕人而言,似乎顯得有些刺耳,背離了網路時代通俗大眾的價值觀,然而二十年前的我們如果不是「唱高調」,又如何能在台灣的東部築起一道圍籬,始終堅持對於文學美善的信仰?又如何能讓更多有同樣理想之人:廖鴻基、陳列、須文蔚、蕭義玲、許子漢、許又方、郭強生、向陽、方梓、吳明益、甘耀明、鴻鴻、施叔青、羅智成……太多太多實在無法一一列舉,就如同磁吸效應似的,陸續吸引到這座縱谷之中的文學祕境來。
我也常被人問及,為什麼東華大學能夠培養出那麼多文學創作的人才?坦白說我也不知道,開課、演講、座談或是論文會議,固然經常舉行,但每個大學不也都是如此按表操課,大同小異?因此就我私心而言,收穫更大的其實往往是課餘之後的清談,尤其在楊牧老師的宿舍或是花蓮市區的樸石咖啡館,大夥兒經常聚在一起聊到夜半時分,還流連依依捨不得散去,若用「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來形容,似乎有點自誇,然而彼此相聚時的歡愉光彩,機智的笑語交鋒,不斷擦亮了我們理性和感性的利刃,當時只道是每日的尋常,如今想來卻是人生中何等珍貴難得的緣分。
故就這點而言,我是無比幸運的,在台大這座自由開放的學府從大學讀到博士,總共十一年之久,畢業後又因緣巧合去到東華大學,一個與台灣西部隔絕,面對太平洋故竟比台大還要更形開闊的新天地,又度過了被海洋和山脈環繞的十二年歲月,與師長同儕們一起盡情編織文學的美夢。幾部大塊頭的文學經典:《追憶逝水年華》、《浮士德》、《尤里西斯》、《奧德賽》、《伊里亞德》……我都是在這幾年中把它細細讀完,更不用說我鍾愛的幾位導演:柏格曼、帕索里尼、荷索、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也被我用繫年的方式,日日在家為自己一人舉辦小型的影展。過去在台北心情浮躁,總是難以進入這些偉大創作者的深邃世界,而如今來到了花蓮,忽然一切都沉靜下來,竟恍然大悟那些白紙黑字和光點交織成的影像,到底在向我訴說些什麼?
令人泫然欲泣的耳語,當生活的表象全都被一一剝除之後的,赤裸而寂寞的心,原來我讀書寫作了這些年,直到此刻才真正懂得了文學。那時的我住在花蓮港海岸路旁的一棟大廈十樓,每天面對無邊無際的藍色太平洋,而終日埋在這些「唱高調」的文學電影中,還有古典音樂作伴,生活非常的不接地氣,但卻又非常確切地抉住自己幽暗的內心。在花蓮看不到日落,只有日出和月升,而我更偏愛的是後者,每當一輪皎潔的明月自黑暗的海面上冉冉升起,我目睹此一景象,心裡總不禁要默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但究竟要和誰共此明月呢?那時正值三十歲的我其實不太在乎,文學為我注滿了樂觀的活力,就像是太平洋上的那輪明月般光輝,我相信未來還有無限的可能,就像是花蓮綠意盎然的大地,七星潭波濤洶湧的浪花,以及鵝卵石生生不息的歌唱,這是一座沒有冬天的國度,所以就連黑夜也是無比的光明燦爛。
我們也愛夜晚的太魯閣更勝白日,白天是屬於觀光客和旅遊手冊的,而夜晚卻變成了我們獨享的探險天堂,黑夜中高聳的峭壁發出金屬般的冷冽光澤,一輪明月高懸,更照得整條蜿蜒的山路如同鏡子一般發亮。每當我一開車走入燕子口,山壁就忽然唰地低矮下來,而我們就像是落入一個巨人的口中,戰戰兢兢滑行過他崎嶇的齒縫,又像是闖入一座夜間的樂園,搭上雲霄飛車在山巒之間一會兒降落,一會兒爬升,一會兒又加速全力奔馳。文山溫泉總是我們夜遊的終點,好幾次還帶上了火把和蠟燭,在溫泉池旁點燃了一圈小小的火光,彷彿野人獻祭似的。我們裸身浸入滾燙的泉水,等到熱得受不了了再爬起來,跑到旁邊的溪流,躺在河床上讓冰凍的水流沖刷自己的四肢,一抬起頭,便見到了滿天密密麻麻的星斗。
那是我永生不能忘記的,流過太魯閣峽谷的銀河,繁複的星圖從山巒與森林的陰影中浮出,宛如密碼,訴說著神祇對於這片土地的慷慨恩賜。我聆聽著嘩啦啦的溪流聲,忽然想起楊牧老師在《時光命題》後記中的預言:「二十一世紀只會比這即將逝去的舊世紀更壞——我以滿懷全部的幻滅向你保證。」然而也想起了楊牧老師的詩〈花蓮〉:
「你莫要傷感,」他說:
「淚必須為他人不要為自己流」
海浪拍打多石礁的岸,如此
秋天總是如此。「你必須
和我一樣廣闊,體會更深:
戰爭未曾改變我們,所以
任何挫折都不許改變你」
當時我已經隱約預感到,未來人生必經的一連串挫敗與幻滅,但花蓮壯闊的山和海彷彿在向我證明永恆的可能,那不曾改變也不許改變的抽象事物,因為這裡已是一切的峰頂。
我在花蓮教書已快十年了,但對於山風海雨的景色,卻未嘗感到一絲厭倦過。每一次,都彷彿是初相見,不禁要為它不同的顏色和姿態,暗自訝異起來。尤其是當乘坐北迴線的火車時,過了宜蘭、羅東,進入隧道,在一片漆黑之中,我就忍不住要猜測,等一下,火車出了隧道之後,將會看到一個什麼樣的太平洋呢?是金光閃爍?白浪奔騰?還是平靜而幽暗的呢?海洋的變幻莫測,就如同是人一般,也自有它秘密底心事。
奇怪的是,分明同樣都是大海,但是蘇澳以北的海,卻和以南的海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面貌。在台灣的東北角,一如它多雨而且陰霾的氣候,海洋也恆常是黝黑而沈重的,彷彿是累積了滿腹的情緒,而沿岸銳利的礁岩,更多添了蕭瑟的氣氛。然而,一旦越過了山,來到東部名為「和平」的小站之後,海洋就忽然變得豁然開朗了起來,就連天氣也都在一剎那之間,就放晴了似的,見到明媚的陽光。「和平」,這是一個讓人看了就忍不住會心平氣和的地名。所以我總覺得自己搭一趟火車,就像是經歷了兩種季節,從秋季一路走到了夏季,而我的個性,卻始終是屬於夏日的,眷戀著陽光的溫度和海洋的氣味。也因此,每當沿著海岸線,從東北角往花蓮下行時,我的心情也被窗外的景色一點一滴照耀得歡喜起來。
不過,我也始終不能夠理解,為什麼在和平附近的車站月台旁邊,要築起一道灰色的水泥圍牆,遮擋住前方的風景呢?以致每一次經過時,我都得要從座位上站起身來,才能越過那堵難看的圍牆,眺望遠方藍到發亮的太平洋。還有那令人無法視不而見的發電廠、水泥廠,實在談不上好看的龐大建築物,以及被挖得有些破損的、半禿的山谷,就像是看到一個純真的孩子身上,卻出現了難以遮掩的殘缺,令人不免感到微微的心痛與遺憾……。「和平」,原來也不是那樣和平的啊。
過了清水斷崖,太魯閣,再往下行,沿著台九線,就會走進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所構成的綠色長廊。在高聳的奇萊山峰注視之下,花蓮的城鎮便在狹長的縱谷平原中,以小小的規模零星散佈開來,而東華大學就位在其中之一,躲在山的懷抱間。每天,我從研究室走出來,一抬起頭,看見的無非就是山巒,而不是大海。因為太平洋已經被海岸山脈遮擋在另外一邊了,然而,海其實一點也不遙遠,只要開車繞過低矮的山巒,不出十分鐘,便會見到遼闊的大海,一望無垠,坦蕩蕩地在眼前攤開。而我最喜歡做的事,莫過於搭船出海了,從海面的角度,再轉身回看台灣島,便會發覺海岸山脈竟是如此的可愛,它溫馴地、謙卑地伏在海邊,護衛著居住在島嶼邊緣的子民們。而花蓮便沈睡在這片山脈與海洋的天然屏障之間,寧靜,祥和,與世隔絕,雖然颱風、地震時而發生,但是傳說中可怕的海嘯,卻不曾到來,因為這兒是一塊被山與海所祝福的淨土。。
然而,這兒也不全然是祥和的,寧靜的,破壞伴隨著建設,正在一點一滴地發生當中。就在我來花蓮的短短十年間,山與海的模樣,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七星潭改變了,海岸倒退,而在怪手的屢屢挖掘之下,石灘也在日漸縮小,不知道為了什麼,七星潭變得不再可親起來,而昔日素樸的海灘,曾是當地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乘涼、散步、玩水、野餐,但如今的海岸,卻多了一些觀光的裝飾、涼亭、步道,但卻距離大海更加遙遠了,而過去逐浪的快樂,也漸漸地失去了。
太魯閣亦是如此。它的山壁險峻、高聳、光潔而壯美,在太陽的照射之下,彷彿會反射出金屬的光澤來,令人不寒而慄,又彷彿是穿行在巨人崎嶇的齒縫,一不小心,就會被吞下無邊無際的黑暗中。然而,就連太魯閣也是如此的脆弱。幾乎每一次,我來到山裡,都會看到它正在修修補補,千瘡百孔,山壁上彷彿貼了無數塊的膏藥,而颱風一來,這些傷口又要發出一陣哀嚎。在我的記憶中,最為難忘的文山溫泉,原是一座天然的水池,傍著山壁,泉水溫度雖高,但只要一咬牙,浸泡下去,就會覺得全身上下的毛細孔都刺痛發麻,又因為臨著野溪的清涼,而感到格外的舒暢。我曾經躺在溫泉旁黑暗的溪谷中,仰望燦爛的星斗,灑在山巒與樹木的陰影之上,但如今,如此甜美的經驗,卻已不可再得了,文山溫泉也因為土石崩落,而成了禁地。大自然正在慢慢地改變它的面容。
也因此,身在花蓮,更多了一些矛盾的心情。我們目睹著自然的壯麗與大美,但也目睹它一日復一日的傾頹,改變。砂石車輾過木瓜溪的溪谷與河床,也輾過了花蓮港前那條美麗的海岸公路,颳起一陣陣紙漿廠散發出來的臭氣。而那條馬路,雖然被規劃成為一條散步、飲食、騎單車和遊憩的專屬道路,但是卡車的呼嘯往來,猖狂橫掃路旁的椰子樹,早就讓這裡成為一條令人膽戰心驚的危險公路了。更不消提,在還未建造花蓮港之前,這一帶的海洋是如何的安詳與靜謐了。據說,那時候的人們很容易就能夠親近大海,而海邊還有大片大片的鵝卵石灘,潔白的石頭就在浪花的淘洗與滾動之下,形成了千奇百怪的顏色與圖案……
海洋和山,正在逐步地遠離我們。花蓮長長的海岸線,被丟擲下無數的消波塊,彷彿是在告誡人們,大海是可怕的,欲除之而後快;而山,竟也開始令人恐懼起來。沿著花東縱谷再往下行,來到光復、大興,便依稀可見颱風土石流所帶來的災難,為這個富饒的平原上,抹上了一層濃重的陰影。
因為,山也是變幻莫測的啊,像人一般,自有它秘密底心事。
所以如今的我,更喜歡的卻是一些未曾被命名,未被柏油馬路穿越,也未被觀光旅遊指南發現的小地方了。隨便選條小徑,穿過木麻黃林,就能來到海邊,踩一踩雪白的浪花。我還曾在某個午後,在某個小村落的海邊,遇到了成千成百的烏鴉。我猜想,它們應該是從距海不遠的山脈飛過來的吧。聽說,烏鴉最喜歡啄人的腦袋了。但或許是我太過浪漫,我總覺得,牠們一點敵意也沒有,正當我躺在白色的鵝卵石灘時,烏鴉群集,飛到我的上方,幾乎遮蔽掉了大半的天空。牠們發出嘎嘎的大聲叫嚷,震耳欲聾,離我非常之近,但卻並未啄我,只是在猛烈的海風之中,反覆地在我身旁盤旋、環繞著,許久許久,徘徊不去。牠們彷彿是在焦急地對我訴說著些什麼,口乾舌燥,說了又說。
莫非牠們是在訴說,關於花蓮山與海秘密底心事嗎?還是在說,大自然的純樸與美麗,其實一直在不斷流失當中。於是生活在這一座保守的、步調出奇緩慢而看似一成不變的小城裡,我卻深深感到,某種迫切焦慮的改變,也在無時無刻地入侵當中,而那即將消失不見的,恐怕不僅是山,是海了,還更是某種生活的風格,某種價值的取捨,以及某種難以言喻的,關於美的感受。



